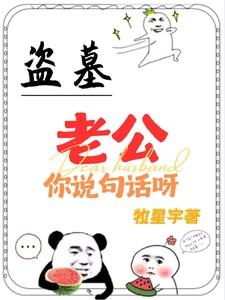吞噬小说>在时光里聆听巴蜀回响 > 第180章 巴蜀彝韵 凉山深处的血脉与烟火(第2页)
第180章 巴蜀彝韵 凉山深处的血脉与烟火(第2页)
烟火里的智慧
扯勒部的人懂生意,也懂生活。叙永的集市上,他们的摊位总最热闹:卖草药的老婆婆背着竹篓,用带着彝语口音的四川话吆喝“天麻补气血哦”;打银器的小伙敲着小锤,银镯子上一边刻彝文“吉祥”,一边刻汉字“平安”。最绝的是“扯勒米酒”,用糯米和高粱混酿,装在土陶坛里,开坛时香气能飘半条街。
“我们扯勒人,像山间的藤,能缠树,也能绕石。”古蔺的酿酒师傅说,他的酒坊传了四代,秘诀是“三借”:借汉族的酒曲、借苗族的蒸馏法、借彝族的陶坛储存。酿出的酒,既有川酒的烈,又有彝酒的绵,去年还得了省里的奖。现在,他的儿子在网上卖酒,直播间里摆着扯勒部的绣花布,下单就送块绣着太阳纹的杯垫,“要让全国人都知道,川南有个会酿酒的扯勒部。”
叙永的老街上,还有家“扯勒银铺”,老板能打彝族的太阳纹手镯,也能做汉族的龙凤呈祥银锁。“客人要啥样,我就打啥样,”老板笑着说,他的手艺是爷爷传的,爷爷年轻时跟着汉族师傅学过,“手艺不分民族,能让人喜欢就好。”去年有个外国游客来买银饰,他特意在银片上刻了彝文“友谊”,游客看不懂,却宝贝得很,说“这上面有中国的味道”。
五、红彝:金沙江边的火焰人家
攀枝花的金沙江畔,红彝的村寨像撒在山坡上的玛瑙。阿署达村的房屋刷着红漆,屋檐下挂着玉米串,金黄的穗子在风里摇晃,与红彝姑娘的鸡冠帽相映成趣。“我们的红,是太阳给的。”村里的阿婆摸着孙女的帽子说,银泡在阳光下闪着光,红绒球像一团团小火苗。
迁徙的红
红彝自称“乃苏颇”,明朝洪武年间从南京迁徙而来。村口的黄葛树已有六百岁,树洞能容下两个孩子,老人们说,当年祖先就在这树下搭起第一座草房。树旁的石碑刻着迁徙路线,箭头从江苏指向四川,像一条看不见的血脉,连着遥远的故乡。
红彝的“红”藏在细节里。女子的百褶裙用七彩土布拼缝,裙摆绣着“江水纹”,据说是为了记住渡过的金沙江;腰间的红腰带用羊毛纺成,要缠七圈,寓意“七步平安”。最特别的是“鸡冠帽”,硬布做的帽架上缀满银泡,红流苏垂到肩头,“这是金凤凰变的,当年它引路,我们才躲过瘴气。”阿婆指着帽顶的红绒球,眼里闪着光。去年村里的姑娘们做了新帽子,在银泡里嵌了小led灯,晚上跳舞时亮闪闪的,“既要像祖先那样守着红,也要像年轻人那样追着光。”
红糯饭里的日子
红彝人过年,要把日子过成红色。除夕前三天,阿署达村的炊烟就带着特殊的香气——那是血糯饭的味道。凌晨五点,各家的灶台就亮起了火光,男人们负责杀猪,将温热的猪血盛在陶盆里,女人们则把浸泡了整夜的糯米倒进猪血中,双手反复揉搓,直到每粒米都裹上猩红的外衣。
“猪血要鲜,糯米要圆,还得加把红米,”阿婆边揉米边念叨,她的指甲缝里总嵌着红色的米浆,像是常年戴着红戒指,“这样蒸出来的饭,红得扎实,日子才能红火。”蒸饭用的是竹制蒸笼,铺着新鲜的芭蕉叶,蒸汽从笼盖的缝隙里钻出来,带着芭蕉叶的清香和猪血的醇厚,在厨房里绕成一团暖雾。
蒸好的血糯饭盛在竹簸箕里,红得亮,像一颗颗凝固的太阳。孩子们早就围着灶台转,趁大人不注意,偷偷捏起一团塞进嘴里,糯米的黏甜混着猪血的微腥,是红彝孩子最惦记的年味。阿婆会把糯饭分成小份,让孩子们送给邻里,“一家的红不算红,百家的红才叫年”。去年我在村里,亲眼见七岁的小姑娘阿果捧着糯饭,踮脚敲邻居家的门,门一开就脆生生喊:“阿普阿么,我家的红饭熟啦!”门里立刻传来笑声,接着递出一小袋核桃,“给果儿当零嘴。”
初一清晨,拜年的队伍像条红绸带,在村寨里蜿蜒。孩子们穿着新衣,捧着血糯饭,挨家挨户说吉祥话。长辈们早就在堂屋等着,接过糯饭,回赠一双绣着红丝线的鞋垫。阿婆给我看她收藏的鞋垫,针脚细密得像鱼鳞,上面绣着“太阳花”和“脚印纹”,“这是说,脚下有红运,步步踩吉祥。”她年轻时收到的鞋垫,现在还垫在鞋里,红丝线磨得白,却依然暖和。
红彝的宴席上,“红炖肉”是压轴的硬菜。选最肥的五花肉,切成巴掌大的方块,先用红糖炒出糖色,再倒上酱油、花椒、八角,在土陶罐里慢炖三个时辰。揭开罐盖时,肉香能飘半条街,肉块红亮得像玛瑙,筷子一戳就透,肥油顺着筷子往下滴,却一点不腻。“炖肉要像过日子,急不得,”掌勺的阿叔说,他炖肉时总在灶边摆个小板凳,时不时添块柴,“火太旺会焦,火太弱不香,得像金沙江的水,慢慢淌才有力道。”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吃炖肉时要配自酿的荞麦酒,酒是红彝人用土法酿的,装在陶坛里,开坛时要先敬灶神,再敬祖先。酒碗是粗瓷的,碰在一起“哐当”响,喝到兴头,就有人唱起酒歌:“红米饭,炖肉香,客人来了心花放;一杯酒,敬太阳,日子过得比蜜甜……”歌声里,有人敲起了月琴,琴弦拨动时,像金沙江的水在石头上跳,把满桌的红,都唱成了流动的诗。
手艺里的红火
红彝人被称为“浪购”——有手艺的人。这话在阿署达村的老木匠阿普身上,体现得最真切。他的木匠铺在村口的老黄葛树下,工具摆得整整齐齐:牛角柄的刨子、雕花的刻刀、磨得亮的斧头,最宝贝的是一把传了三代的锛子,木柄上包着铜片,是他爷爷年轻时在金沙江畔捡到的铜料做的。
“红彝人的手艺,要像红糯饭一样,得有嚼头。”阿普边说边刨木头,刨花像雪片一样落在脚边,带着松木的清香。他会做雕花的马鞍、带铜饰的木箱,最绝的是“红彝婚房床”。床架上雕着“喜鹊登梅”,却用彝绣的纹样;床楣挂着红布缝制的“葫芦香囊”,里面装着艾叶和花椒,据说能驱邪祈福。去年村里的小伙结婚,特意请阿普做床,他熬了三个通宵,在床腿上刻了“迁徙图”,从南京到攀枝花,一路的山水都缩在巴掌大的木头上。
阿普的工具箱里,还藏着些“新玩意”。有次我看见他在木头上钻小孔,问他做什么,他神秘地笑,从口袋里掏出个小小的蓝牙音箱,“要把这玩意儿装进去,让年轻人的婚床,既能听见祖先的话,也能放流行歌。”他边说边试音,音箱里传出彝族歌手的《敬酒歌》,和刨木头的声音混在一起,竟格外和谐。
村里的姑娘们,把红彝的手艺玩出了新花样。阿果的姐姐在网上开了家“红彝绣坊”,直播间里,她穿着鸡冠帽,教网友绣“太阳花”。她的绣线除了传统的红、黄、黑,还加了薄荷绿、浅紫色,“城里的姑娘喜欢亮堂的颜色。”去年她设计的“鸡冠帽挂件”卖得特别好,小小的帽子缀着银泡和红绒球,能挂在包上,“让红彝的红,跟着年轻人走四方。”
有次我看见她们在绣一块大桌布,图案是“阿署达全景图”:金沙江绕着村寨,黄葛树在村口扎根,远处的钢城攀枝花闪着光。“这是要送给市里的博物馆,”阿果的姐姐说,针脚在布面上游走,像在画一幅立体的画,“让后人知道,红彝人既守着老手艺,也望着新日子。”
火塘边的传承
傍晚的阿署达村,火塘成了最热闹的地方。松木在火塘里噼啪作响,把墙壁映得通红,老人们围坐一圈,抽着旱烟,给孩子们讲迁徙的故事。“当年祖先从南京来,背着锅碗瓢盆,踩着木筏过金沙江,”阿婆的声音有些沙哑,却带着穿透力,“有人问,为啥要走这么远?祖先说,哪里有太阳,哪里就能扎根。”
孩子们听得入迷,眼睛瞪得像铜铃,追问:“那金凤凰真的引路了吗?”阿婆笑着摸孩子的头,指着火塘里的火苗:“你看这火,烧完了变成灰,明年开春撒在地里,土豆会长得更壮。我们红彝人,就像这火,不管到哪,都能把日子烧得旺旺的。”
去年火把节,我又去了阿署达村。村里的年轻人用无人机在夜空拼出“凤凰”的图案,老人们则在地上摆起“太阳阵”,用火把围出圆形的图案。红彝姑娘们穿着新做的鸡冠帽,帽檐的led灯闪闪烁烁,和天上的星星连成一片。她们跳着新编的“迁徙舞”,脚步踩着电子乐的节拍,却依然保留着祖先的韵律——前进时像渡江,转身时像绕山,抬手时像托举太阳。
阿普的木匠铺里,新做的鹰形木雕摆了一地,每个木雕的翅膀上,都刻着一行小字:“根在红土,志在远方。”他说要把这些木雕送给村里的孩子,“让他们知道,红彝人可以去城里读书、工作,但心里不能忘了这山、这水、这火塘的暖。”
离开时,金沙江的水在夕阳下泛着红光,像一条流淌的红绸带。阿婆站在村口的黄葛树下,朝我挥手,她的白在晚风中飘动,手里的红布条也跟着摇,像在说:红彝的故事,永远是未完待续的红。
六、火塘边的答案
凉山的秋夜来得早,火塘里的松木噼啪作响,把诺苏老人的脸映得通红。他听我问起那些支系与划分,突然笑了,露出没剩几颗牙的嘴。
“黑彝白彝,就像火塘里的两块炭。”老人用树枝拨了拨火,火星子溅起来,又慢慢落下,“一块烧得旺,一块烧得慢,最后都成灰,混在一起,肥了地里的土豆。”
他指着窗外的山,月光正照在梯田上,像铺了层银霜:“诺苏、古侯、曲涅、扯勒、红彝,像这山上的树。有的长在东坡,晒得多;有的长在西坡,淋得雨多;有的长在山脚,离水近。样子不一样,可根都扎在同一片土,风一吹,叶子都往一个方向摇。”
火塘边的铜壶烧开了水,水汽模糊了窗玻璃。远处的村寨传来歌声,分不清是诺苏的酒歌,还是红彝的调子,只觉得像金沙江的水,温柔又有力地漫过心田。原来巴蜀大地的彝韵,从不是孤立的音符,而是无数支系的声线,在时光里交织成的歌——唱着迁徙的路,唱着火塘的暖,唱着血脉里的坚韧与温柔。
天亮时离开山寨,晨雾已经散去,阳光洒在梯田上,荞麦花在风里摇晃。远处的经幡还在飘,红、黄、白三色融在蓝天下,像在说:这里的故事,永远未完待续。
喜欢在时光里聆听巴蜀回响请大家收藏:dududu在时光里聆听巴蜀回响小说网更新度全网最快。

![[清穿+红楼] 太子和我的狗】互穿后](/img/18957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