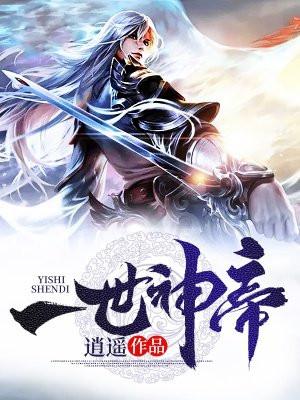吞噬小说>手握金手指,在三国当天命之女 > 第229章 禹王转世(第1页)
第229章 禹王转世(第1页)
王镜不仅身负军务重任,还要应对民生大事。所幸在黄河水患来临前,她已提前修缮水利,辖地内大部分地区未受重创,唯独徐州受灾严重。
黄河在兖州东部,濮阳至济阴段决口,汹涌的洪水顺着泗水一路南下,淹没徐州。
下邳地势低洼,当其冲,如今城内积水已没过膝盖,东海郡的盐场被洪水摧毁,更可怕的是大片农田被淹,秋粮绝收可能引的饥荒。徐州可是养活万人口的大州……
徐州下邳
陈登站在下邳城残存的城墙上,望着城外已成泽国的景象,心痛如绞。
泗水暴涨的浊流冲垮了堤岸,混黄的河水裹挟着断木、茅草甚至牲畜的尸体,在原本富庶的平原上肆意奔流。远处几处高地上,密密麻麻挤满了逃难的百姓,像一群受惊的蚂蚁。
“大人,东门外的三个村子全淹了……济阴那边决口太大,洪水来得太快……”
郡丞匆匆赶来,官服下摆沾满了泥浆,模样狼狈。
陈登闭了闭眼。作为徐州刺史,他比谁都清楚这场水患意味着什么。
《墨子·七患》所言:“国有七患,水患居其一,失政则天灾人祸并至。”这次水患既是天灾也是人祸,只是最终受苦的却是流离失所的穷苦百姓……
他转身时,声音已经恢复了沉稳,下令道:“立即做三件事。第一,征调所有能用的船只,把困在屋顶树上的百姓接到高地;第二,打开广陵、琅琊两处粮仓,在避难所设粥棚;第三,派人去决口处查看,准备堵口材料。”
命令一道道传下去,整个徐州官府像被鞭子抽打的陀螺般急运转起来。陈登亲自带着医官巡视各个避难所,看到的是挤在草棚下瑟瑟抖的灾民,孩童的啼哭与老人的咳嗽声此起彼伏。泥泞的地面上,还有人用树枝搭起简易支架,晾着几件湿透的粗布衣裳。
有老农跪地哭诉,声音哀切:“刺史大人!我家三十亩稻子全泡汤了,这可怎么活啊……”
陈登扶起老人,“老人家且宽心,昨夜我已命人在城隍庙设粥棚,先安置受灾百姓。”
见老人浑浊的眼中泛起泪光,他又从袖中掏出块碎银塞进老人掌心,“这点银子先买些吃食,明日辰时到刺史府,我亲自登记受灾田亩。”
老人感激而去。身后医官低声道:“刺史大人,已备好了驱寒姜汤,每隔半个时辰便会煮上一锅,免得百姓着了风寒热。另外,我们组织了人手,将遇难者的遗体集中收敛,用石灰深埋,并在四周洒了雄黄粉,防止疫病滋生。”
陈登微微颔,目光中难得露出一丝欣慰。他转身拍了拍医官的肩膀:“此番辛苦诸位了。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让疫病横行。”
说着,他望向雨幕中忙碌的衙役与医者,心中暗自盘算着明日的赈灾安排,必须尽快搭建更多避雨棚,还要联系周边州县调配粮食……
当夜,刺史府临时迁到了未被淹没的西城。陈登在油灯下查看各地急报,眉头越皱越紧。决口处水流太急,传统的夯土筑堤根本立不住;各地粮仓存粮最多支撑半月;最棘手的是,已经有流民开始聚众闹事。
就在这时,亲卫冲了进来。
“大人,丞相府急件!”
陈展开一看,紧绷的面容突然松动。
“……已备救灾物资,明日即达。水泥遇水凝,防水布可作临时堤坝,愈炎散治热症有奇效。另拨五万石粮经淮水运往下邳。”
次日正午,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出现在下邳城外。车上满载从未见过的物资,银光闪闪的卷状物、灰白色粉末装在奇怪布袋里、透明琉璃瓶中的药片……带队的是个精瘦汉子,自称是王镜麾下工程营校尉。
校尉扯开一卷银色材料,这布料韧性极好,在阳光下泛着奇异光泽。他介绍道:“这叫防水布,展开有二十丈长,主君说用它垫底,再压沙袋,洪水冲不走。”
陈登亲自带人试验。当防水布铺在决口处,湍急的水流果然无法将其卷走。民夫们欢呼着将沙袋垒上去,以往需要半月才能堵住的缺口,三天就合龙了。更神奇的是那种叫“水泥”的灰粉,加水搅拌后倒进木框,不出两个时辰就硬如岩石。
与此同时,另一批物资被分到各个避难所。灾民们领到巴掌大的方块,疑惑地听官吏解释:“这一小块能顶一天饿。”
有妇人将信将疑地咬了一口,干硬的口感后是浓郁的麦香,她瞪大了眼睛惊叹:“神仙粮食啊!”
医官们拿着透明小瓶里的药片如获至宝。高热不退的病人服下后,次日竟能坐起来喝粥。净水设备更让百姓啧啧称奇,浑浊的河水经过那个铁罐子过滤,竟变得清澈甘甜。
几日后,陈登巡视新建的临时营地。整齐的帆布帐篷取代了漏雨的草棚,每顶帐篷前都挖了排水沟。远处,新疏浚的河道里,民夫们正在清淤。
随后,又有一批睡袋运到了下邳城西的高地避难所。灾民们围拢过来,好奇地打量着这些从未见过的物事。方方正正的布包,用某种光滑如丝的布料缝制,捏上去却蓬松柔软,像裹着一团云朵。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分物资的小吏扯开捆扎的布带,睡袋立刻像花朵般舒展成一条筒状物。他示范着钻进去,只露出个脑袋,“这叫睡袋,夜里钻进去,风雪都侵不透。瞧,底下这层防水布能隔开地气,里头填充的是棉花,比十床芦花被还暖和。”
张五壮着胆子摸了摸,指尖立刻陷进惊人的柔软里。他喉头滚动了一下:“官爷,这……真给我们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