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噬小说>穿成吕雉心尖崽番外 > 6070(第2页)
6070(第2页)
梁王殿下与张侍中功在千秋,要赶快给师叔们分享分享。
于是奉常叔孙通经历了最为忙碌的一天。
待在长安的儒门大贤,一个也不能落下通知!上回说他圆滑的师叔,送一叠草纸就行。
出于谦逊的意图,目前人多势大的黄老家大贤,他需上门拜访;出于友好的意图,被将军们信赖的法家大贤也不能落下。至于墨家?哪儿凉快呆哪儿去,长安城好像没有墨家的传人,应该死绝了吧。
叔孙通暗暗思索,脚步不停,跑得都要口吐白沫了,终于让“纸”在长安城的学术圈扬了名。
其中也有太后的授意,不知大贤都是什么反应呢?
一小部分人陷入了恐慌,绝大多数人欣喜不已。
撇去恐慌者认为纸张便宜,恐会造成民间向学的热潮,从而破坏精英传承,破坏师门结构的纯净,多数欣喜者暗暗点头,热泪盈眶,觉得能看到纸的诞生,实在是不枉此生了。
等回过神来的时候,他们陷入了呆愣。
有白发苍苍的老者叫住叔孙通:“通啊,你说这是谁出的点子,谁负的责?”
叔孙通忍着脚痛,恭敬回答:“是梁王殿下出的点子,张不疑张侍中负的责。”
老者:“……”
老者怀疑自己耳背了:“你再重复一遍。”
叔孙通感慨道:“梁王殿下向陛下借人借地,正是因为此事,所研制的纸张,实则是献给太后的孝心。留侯世子也颇有其父之风,师伯,您觉得呢?”
老者震惊:“梁王他——”
叔孙通:“梁王他很快就要过五岁生辰了。”
老者:“…………”
这可真是英雄出少年,也出童年。
这厢,学术圈动荡不歇,收到草纸以及附赠说明的儒门大贤面红耳赤,堪堪没有气晕过去。
叔孙通就差上门和他唠嗑,说:“师叔啊,您说梁王不务正业,现在看来不是这样的哦。”
那厢,向皇帝进谏“梁王扰民”的潜邸大臣,则是又羞又愧,恨不能用自尽来洗刷耻辱了。
陛下没有责骂他,而是遣人将白纸摆在他的案头,这叫他要如何做人,日后如何进宫议政?
他不懂这叫兄长的暗中炫耀,也不懂这叫打脸诛心,此时后悔如潮水般涌来,伴随着指数性增长的警惕,重重敲在他的心上。
一个悚然的念头冒出,梁王多智近妖,对陛下来说,真的是喜事吗?
陛下非但没有提防幼弟,也没有抹去梁王的功劳。长此以往,若纸替代竹简,梁王将会俘获天下读书人的心,岂不是……岂不是……
他摇摇欲坠,面色惨白,捧着御赐的白纸像捧着烫手山芋。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宫外炸锅的时候,梁王殿下终于醒了。
他慢吞吞地起床,洗漱,穿好衣裳佩好迷你剑,怀揣着对庄园的憧憬之心,幸福地迈出卧房。
入眼便是奋笔疾书的吕禄,刘越眨眨眼,睡出红痕的面颊写满欣慰。
他安安静静地往膳室走,不欲打扰勤奋的表哥,走到僻静的拐角处,步伐停了停,像是踩上了什么东西。
刘越垂头一看,是一张折叠的白纸。
不知是谁掉落在这里……灰黑色的眼睛充斥大大的疑惑,他俯身捡起来,展开,其上用小篆写着四个大字——“五年学武”。
“五年”后面,原本跟着“教学大计”,似是书写之人不满意,又把它划了去。
笔锋并不圆融,满是锋锐的气息,刘越彻底呆在了原地。
第62章
刘越沉默地站着,不明白为什么会突兀地出现一个“五年练武”,加上前面划去的字迹,应当是韩师傅的手笔。
让他害怕地想起便宜爹主导的五年计划,虽说被可亲可敬的太傅兼养生友人否决了,但雁过留痕,曾经深深地震撼了他的小心灵。
梁王殿下在与武师傅真诚交谈,还有膳室用膳两个选择中纠结,一秒,两秒……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摸摸肚皮,有些瘪,饥饿的感受悄悄弥漫。
刘越凝重地叠好白纸,藏到衣襟里,天大地大吃饭最大,有什么事,吃完再说好了。
半个时辰后。
寝宫后殿的竹林里,彭越收好热身的铁锤,奇怪地问韩信:“韩兄,你那张动过笔的纸呢?”
都赖他们天才又聪明的大王,而今不必用笨重的竹简书写计划,彭师傅不知从哪顺来了笔墨,怂恿着韩师傅试一试。
于是大标题一挥而就,只经历了一次涂改。
写完发现纸张不见了,莫不是从袖口滑下,掉在哪个角落了?
韩信拧眉,只说不知。
彭越挠挠头,随即不再去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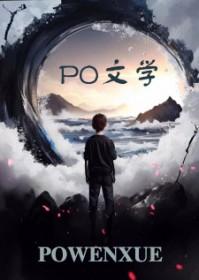

![野望[重生]+番外](/img/1708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