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噬小说>重生后我成了暴君心尖宠 > 第157章 新的挑战(第1页)
第157章 新的挑战(第1页)
初冬的第一场雪落进皇城时,御书房的烛火已燃到了第三根。容珩放下北境急报,指节在奏折上重重叩了三下,积雪压断梅枝的脆响从窗外传来,竟与他心头的沉郁莫名呼应。
“李德全。”他扬声道,声音里带着未散的寒意。
“奴才在。”李德全轻步走进来,见案上的急报边缘已被捏出褶皱,心头一紧——自打北境安定了五年,陛下已有许久没这样动过怒了。
“传朕旨意,召六部尚书、大将军、萧元帅即刻到御书房议事。”容珩起身时,龙袍下摆扫过案角的青铜镇纸,出沉闷的碰撞声,“再让东宫太子也过来。”
李德全刚要应声,却见卫蓁蓁披着件狐裘披风走进来,手里捧着个暖炉:“陛下忙了一下午,先喝口热茶暖暖身子。”她瞥见那封急报,封皮上印着的“北境密报”四个字刺得人眼疼,便知定是出了大事。
容珩接过茶盏,滚烫的茶水却暖不透指尖的寒凉。“北漠王庭换了新主,是老狼王的幼子,名叫赫连烈,刚登基就动了歪心思。”他沉声道,“昨日三更,北漠铁骑突袭了咱们的雁门关,虽被守将打退,却掠走了附近三个村落的百姓,还放话说……要咱们割让河西三郡,否则开春就挥师南下。”
卫蓁蓁握着暖炉的手猛地收紧,狐裘披风上的绒毛簌簌颤动。河西三郡是北境的粮仓,更是抵御漠北的屏障,割出去,无异于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她想起五年前,萧沅就是在雁门关浴血奋战,才换得边境安宁,如今尸骨未寒的将士们怕是还在地下不安稳。
“赫连烈这是仗着新君登基,想立威呢。”卫蓁蓁定了定神,声音却依旧颤,“老狼王在位时,虽与咱们偶有摩擦,却知分寸,这幼子……怕是个愣头青。”
“愣头青才更危险。”容珩揉了揉眉心,“他刚上位,急于巩固地位,最可能用对外征战来转移内部矛盾。北漠的骑兵向来凶悍,若真让他们突破雁门关,京城就危险了。”
正说着,李德全匆匆来报:“陛下,六部大人、萧元帅、太子殿下都到了。”
容珩起身整理了一下龙袍,沉声道:“让他们进来。”
大臣们鱼贯而入,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凝重。萧沅刚从军营赶来,玄色披风上还沾着雪粒,肩头落着薄薄一层白,显然是一路策马奔来。容瑾跟在他身后,身上的常服已换成了略显正式的锦袍,虽面带稚气,眼神却异常沉稳。
“都坐吧。”容珩示意众人落座,将北境的急报传阅下去,“情况就是这样,北漠新王赫连烈寻衅,雁门关遇袭,百姓被掠。你们说说,该如何应对?”
兵部尚书率先起身,抱拳朗声道:“陛下,北漠向来欺软怕硬!依老臣看,当立刻增兵十万,驰援雁门关,再派一员大将,直捣北漠王庭,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
户部尚书却皱起眉:“尚书大人此言差矣!如今刚入冬,粮草转运困难,增兵十万,光是军粮就得耗掉国库三成储备。况且河西三郡刚经历过蝗灾,百姓还没缓过劲来,哪经得起大战折腾?”
“那难道就眼睁睁看着北漠欺负到头上?”兵部尚书反驳道,“雁门关守将传来消息,北漠骑兵这几日还在关外游弋,显然没安好心!”
大臣们顿时分成两派,一派主战,说“不打不足以立威”;一派主和,说“当以安抚为主,待开春再做打算”。争吵声越来越大,御书房的烛火被震得摇曳不止。
容珩始终没说话,目光落在萧沅身上。这位镇北元帅自始至终都在翻看北境舆图,指尖在雁门关以西的一处峡谷上来回摩挲。
“萧元帅,你怎么看?”容珩终于开口,声音压过了满堂争论。
萧沅放下舆图,起身拱手:“回陛下,臣以为,主战太过冒进,主和则显懦弱。北漠新王急于立威,咱们偏不让他如愿——既不主动开战,也不能示弱。”
“哦?”容珩挑眉,“说说你的具体想法。”
“第一,增兵三万,而非十万。”萧沅指着舆图,“雁门关现有的守军加上三万援军,足以守住关隘,再多则粮草难继。这三万兵,臣建议从京畿大营调派,都是精锐,能快抵达。”
“第二,加固防线。”他指尖移到河西三郡的边界,“从雁门关到临河城,修一道烽火台,每隔三十里建一座,一旦北漠有动静,两时辰内就能传到京城。再让临河城守将深挖壕沟,囤积滚石、箭簇,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第三,派使者去北漠。”萧沅的目光转向容珩,“但不是去求和,而是去‘问罪’——质问他们为何突袭雁门关,为何掠走我大启百姓。若他们肯放人、赔罪,此事可暂告一段落;若不肯,咱们便有了开战的理由,天下人也会站在咱们这边。”
殿内一片寂静,刚才争吵的大臣们都陷入了沉思。容瑾忽然起身,朗声道:“儿臣觉得太傅说得对!就像与人打架,得先让对方理亏,咱们动手才占理。”他顿了顿,补充道,“而且修烽火台、挖壕沟,既能防北漠,也能让河西的百姓觉得安全,就像给他们加了层保护壳。”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容珩看向容瑾,眼里闪过一丝赞许:“你说得有道理。民心安定,比增兵十万更重要。”
他转向众臣:“萧元帅的提议,你们觉得如何?”
吏部尚书躬身道:“陛下,萧元帅的计策稳妥!增兵三万既能显威,又不至于耗空国库;派使者问罪,则占尽道义,老臣赞同!”
其他大臣也纷纷附和,刚才的争论声换成了对细节的讨论——谁来领兵驰援?派谁当使者去北漠?粮草如何调度?
容珩看着众人各抒己见,忽然道:“援军统领,朕打算让萧元帅亲自担任。”
萧沅毫不犹豫:“臣,领旨!”
“使者一职……”容珩沉吟片刻,目光落在容瑾身上,“瑾儿,你愿不愿意去?”
满殿皆惊。让刚满十三岁的太子亲赴北漠,这未免太过冒险。卫蓁蓁刚要开口劝阻,却被容珩用眼神制止了。
容瑾愣了一下,随即挺直脊背:“儿臣愿意!”
“太子殿下不可!”礼部尚书急忙劝阻,“北漠新王性情暴戾,万一伤了殿下……”
“正因他暴戾,才更该让他看看我大启的气度。”容瑾朗声道,“儿臣去,不仅是为了问罪,更是为了让北漠百姓看看,咱们不是好战之辈。就像师母说的,治病要先治根,或许这次去,能找到他们寻衅的根源。”
萧沅看着容瑾,眼里满是欣慰:“殿下有这份担当,臣佩服。臣在雁门关接应,定保殿下周全。”
容珩点头:“好!就这么定了。太子明日出,带三十名护卫,再加一名熟悉北漠风俗的通事。萧元帅三日后启程,务必在太子抵达北漠王庭前,把雁门关的防线筑牢。”
散朝时,雪已经停了。卫蓁蓁陪着容珩走在回凤仪宫的路上,踩在积雪上出咯吱咯吱的声响。“陛下,让瑾儿去北漠,是不是太冒险了?”她终于忍不住问道。
“冒险,但值得。”容珩握住她的手,掌心的温度透过厚厚的锦缎传过来,“赫连烈刚登基,内部不稳,未必敢真对瑾儿动手。况且萧沅在雁门关接应,安全无虞。更重要的是,让瑾儿去看看边境的苦,看看北漠的真实情况,比在宫里读十本兵书都有用。”
他顿了顿,望着远处东宫的方向:“他是未来的君主,总得学会在风浪里行走,而不是永远躲在咱们身后。”
卫蓁蓁沉默了。她想起容瑾小时候,第一次学骑马摔破了膝盖,哭着要她抱,容珩却站在一旁说“自己站起来”。如今想来,他对孩子的严苛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期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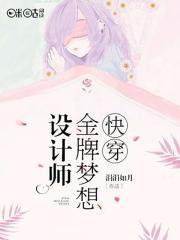

![是怪物,也是爱人[丧尸]+番外](/img/9893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