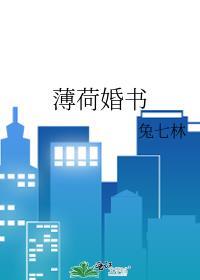吞噬小说>重生后我成了暴君心尖宠 > 第164章 公主的慈善事业(第2页)
第164章 公主的慈善事业(第2页)
百姓们也自来帮忙,老人捡石头,孩子搬碎砖,连那曾被王老三欺负的妇人,都抱着刚做好的鞋垫,给工匠们送去。苏大娘带着绣娘们,在刚砌好的墙头上挂了红绸,说是“讨个喜气”。
三个月后,三十间砖瓦新房在城西立了起来。容玥给这片地方取名“安和里”,取平安祥和之意。乔迁那天,百姓们在门口摆了长桌,各家各户都端来自己做的菜,虽然只是糙米饭、腌萝卜,却摆了满满一桌。容宁被乳母抱着,在人群里咿咿呀呀地叫,小手还指着桌上的野菜团子,惹得个老婆婆赶紧拿起一个,小心地喂到她嘴边。
容玥看着眼前的景象,忽然明白萧太傅说的“善举如星火,能燎原”。暖春社的牌子,已经从坤宁宫的偏殿,变成了安和里的祠堂,里面不仅放着粮物,还多了个“互助簿”,谁家有难处写在上面,邻里看见了就主动帮忙。容瑶画的那些画像,被裱起来挂在墙上,旁边添了新的注脚:“已搬入安和里”“小儿入学”“找到活计”。
入夏那天,容珩和卫蓁蓁来安和里视察。看着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嬉戏,老人们在槐荫下下棋,妇人坐在门口做针线,容珩忽然对萧沅笑道:“朕的女儿们,倒比朕这皇帝做得更接地气。”
萧沅望着祠堂里“暖春社”的匾额,想起柳萱说的,雅诗和明宇都学着给安和里的孩子送书,笑着拱手:“殿下们的心,比炭火还暖,自然能焐热这世间的寒。”
容宁被容玥抱在怀里,小手抓着祠堂门槛上的雕花,忽然咯咯地笑起来。阳光透过雕花窗棂,在她脸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撒了把金粉。容玥低头看着妹妹纯净的笑脸,忽然觉得,这便是最好的慈善——不是施舍,而是让每个生命都能像容宁这样,笑得无忧无虑,活得安稳踏实。
暖春社的故事,渐渐传遍了京城。有商户主动送来布匹粮食,有书生来教孩子们认字,连江湖上的药铺都送来药材。容玥和妹妹们依旧每日来安和里,只是不再需要记账,因为百姓们已经学会了互助;容瑶的画本上,开始画巷子里新开的花、孩子们读书的模样、老人们下棋的专注;容宁也学会了走路,摇摇晃晃地跟在姐姐们身后,给每个遇见的人递上一朵小野花。
卫蓁蓁看着女儿们的身影,忽然想起容珩曾说的“江山是百姓的江山”。此刻看着安和里袅袅升起的炊烟,听着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她忽然觉得,这些便是最坚实的江山——不是金戈铁马,不是玉宇琼楼,而是每个屋檐下的灯火,每双笑眼里的光亮,每颗被温暖过的心。
萧沅和柳萱站在巷口,看着雅诗把自己的绣品送给安和里的绣娘,明宇则和男孩子们比赛爬树,忽然相视而笑。原来这世间最好的传承,从来不是权势地位,而是将温暖传递下去的心意——从皇子的整顿吏治,到公主的慈善事业,从朝堂到江湖,从宫墙到巷陌,像条看不见的河,流淌着,温暖着,让这太平盛世,愈绵长。
入秋时,安和里的槐树叶落了满地,孩子们捡了叶子做书签,夹在容瑶送的启蒙书里。容玥带着妹妹们来看新收的谷子——安和里的百姓在萧沅派人圈出的空地上开垦了亩田,种的谷子刚打下来,金灿灿的堆在晒谷场,像座小山。
“公主尝尝!”去年那个被救的婴儿已经会爬了,他母亲捧着碗新熬的小米粥,非要容玥尝尝。米粥熬得糯糯的,带着股清甜,容玥舀了一勺喂给身边的容宁,两岁的小公主咂咂嘴,伸手还要,逗得众人直笑。
容瑾蹲在谷堆旁,数着新打的谷穗:“这些够安和里的人吃一冬了!明年咱们再多种些,还能酿谷酒呢!”她转头看见容瑶在画晒谷场,忽然指着远处,“四姐快看,柳萱婶婶来了!”
柳萱带着雅诗和明宇,还有几个绣娘行会的妇人,推着辆马车停在晒谷场边。车帘掀开,露出满车的布料和丝线:“苏大娘说安和里的姐妹们绣活好,让我来问问,愿不愿意给宫里的冬衣做些绣样?按件算工钱,不比外面的绣坊少。”
围着的妇人眼睛都亮了。去年跟着苏大娘学绣活的张嫂子搓着手笑:“我们这粗针大线的,能入宫里的眼?”
“怎么不能?”柳萱拿起张嫂子绣的帕子,上面的并蒂莲针脚虽不细密,却透着股鲜活气,“这样的民间样式,宫里还少见呢。”
容瑶立刻拿出画本:“我来画样子!咱们绣些五谷丰登、年年有余的,多喜庆!”容珞则想起库房里有批陈茶,正好给绣娘们提神,当即让人去取。容珠最机灵,拉着柳萱的手问:“婶婶,能不能让我跟着学算账?我想记清楚她们做了多少活,该给多少工钱。”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容宁被乳母放在谷堆上,抓着谷穗往嘴里塞,被容玥笑着抢下来:“这是吃的,不是玩的。”小公主委屈地瘪瘪嘴,忽然看见明宇在追蝴蝶,立刻从谷堆上滑下来,摇摇晃晃地跟上去,两个小不点的笑声在晒谷场滚来滚去。
消息传到宫里,卫蓁蓁正和容珩翻看容瑶画的新绣样,见上面的谷穗沉甸甸的,忍不住笑道:“这孩子,把晒谷场的样子都画下来了。”
容珩拿起张绣着“安和里”三个字的帕子,指尖拂过针脚:“让尚服局收了吧,给各宫分些,也让她们知道,民间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他忽然想起容砚昨日递的奏折,说江南的吏治整顿后,百姓也自组织了“互助社”,忍不住点头,“上行下效,这才是治世该有的样子。”
入冬前,安和里的绣娘们得了第一笔工钱。张嫂子用这笔钱给孩子请了先生,就是去年在暖春社帮忙教书的老秀才;瘸腿的李大叔买了辆新的手推车,靠着给人送货过活;连最胆小的王寡妇,都敢带着绣活去集市上摆摊了。
容玥带着妹妹们来看她们时,正赶上张嫂子的儿子背《三字经》。小家伙背着“人之初,性本善”,眼睛亮晶晶地看着容玥:“先生说,是公主姐姐让我能读书的,我以后也要做个好人。”
容玥心里一暖,忽然想起萧太傅说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她看着安和里新盖的学堂,看着孩子们手里的书卷,看着绣娘们脸上的笑容,忽然明白,慈善不是一时的施舍,是播下种子,等着它长成参天大树。
腊月初八那天,暖春社在安和里办了场腊八宴。百姓们端来各家做的腊八粥,有的放了红豆,有的加了花生,摆了满满一院子。容珩和卫蓁蓁也来了,穿着寻常百姓的衣裳,坐在张嫂子家的炕头上,喝着掺了小米的粥,听着李大叔讲他年轻时走南闯北的故事。
容宁被容珩抱在怀里,抓着桌上的腊八蒜啃,辣得直吐舌头,逗得满屋子人笑。容瑶趁机画下这热闹的场景,画里的皇帝皇后穿着布衣,和百姓们挤在一起,屋檐下的红灯笼映得每个人脸上都红扑扑的。
萧沅和柳萱也来了,萧沅被老秀才拉着对弈,柳萱则和绣娘们讨论新的绣样。雅诗和明宇跟着容瑾去放鞭炮,噼里啪啦的声响里,夹杂着孩子们的欢呼。
容玥站在院子中央,看着眼前的景象——父皇母后和百姓说笑,妹妹们和孩子们玩耍,太傅和先生对弈,柳萱婶婶和绣娘们低语,忽然觉得,这便是暖春社最好的模样。没有公主与百姓的分别,没有宫廷与市井的隔阂,只有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温暖。
宴罢,容珩握着容玥的手,指着安和里的灯火:“你看,这些光虽小,聚在一起,就比宫里的宫灯还亮。”
容玥点头,忽然看见巷口的老槐树上,挂着个新做的灯笼,上面是容宁用朱砂点的小点子,歪歪扭扭的,却像极了天上的星星。她忽然想起刚办暖春社时,那个在雪堆里被现的婴儿,如今已经会跑了,正追着容宁手里的灯笼跑,两个小小的身影在灯火里穿梭,像两团跳动的火苗。
“父皇,”容玥轻声道,“女儿明白了,慈善不是给他们多少东西,是让他们心里也有光。”
容珩笑着摸了摸女儿的头,目光望向远处的京城。那里,容砚正在灯下批阅奏折,整顿吏治的余波还在荡漾;这里,容玥和妹妹们播下的种子,已经了芽。朝堂与民间,刚直与温柔,像一枚铜钱的两面,共同撑起了这太平盛世。
夜深了,安和里的灯火渐渐熄了,只有暖春社的祠堂还亮着盏灯。容玥在账册上写下“暖春社岁末总结”,后面跟着长长的清单:施粥五千三百碗,棉衣七百二十件,救助孤儿十九名,盖房三十间,促成绣活生计二十三家……最后,她写下:“愿岁岁暖春,人人安和。”
容瑶凑过来,在旁边画了朵梅花,说:“明年开春,咱们在安和里种满梅花,像宫里的一样好看。”
容瑾点头:“还要请御膳房的张师傅来,教大家做梅花糕!”
容珠数着新收的捐款,笑道:“我攒的钱够买好多好多花籽了!”
容珞翻开医书:“我查了,梅花瓣能入药,明年咱们可以做些梅花膏。”
乳母抱着打哈欠的容宁,小公主伸出小胖手,抓住账册的边角,咿咿呀呀地像是在附和。
容玥看着妹妹们的笑脸,忽然觉得,这暖春社,早已不是她一个人的想法,而是六姐妹,是父皇母后,是萧太傅和柳萱婶婶,是所有好心人共同的心意。就像那盏挂在老槐树上的灯笼,不是靠一根蜡烛照亮的,是无数根烛芯,共同燃出的光。
窗外的雪又开始下了,轻轻落在祠堂的瓦上,像给这一年的故事盖上了层温柔的棉被。容玥合上账册,心里忽然充满了期待——明年的暖春社,定会比今年更热闹;安和里的梅花,定会开得比宫里的更艳;那些被温暖过的心,定会把这份善意,传递到更远的地方去。
而那个在雪堆里被救的婴儿,那个追着灯笼跑的孩子,那个跟着先生读书的小童,终有一天,也会成为播撒温暖的人。就像萧太傅说的,善举如流水,终会汇入江海,滋养出更繁茂的人间。
喜欢重生后我成了暴君心尖宠请大家收藏:dududu重生后我成了暴君心尖宠小说网更新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