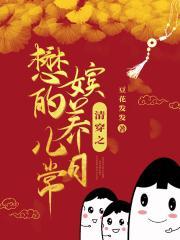吞噬小说>炮灰如何配享太庙(科举)阅读 > 5060(第8页)
5060(第8页)
没由来的,闻清远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他看了看头两张卷纸,除了字小些,书写倒很工整,破题紧合朱子,文风极正,但辞藻不甚瑰丽,还差点意思。
“这不是写的《诗》题吗?送到王路那儿去。”
提调官脸上说不出的神情,哭丧道:“大人,您往后看,他可不止写了《诗》题,他是二十三问都写了!”
“什么!”震惊之下袖子碰到了茶碗,只听得一声脆响,上好的粉彩摔了个四分五裂,闻清远顿感大大的不妙。
若是一般违规也就罢了,这写了二十三篇时文,到底算不算是科场违规也说不清,毕竟科场只规定了士子各认一经,却没说不能写五经。
这事儿自己做不了主,闻清远转头跟仆从吩咐:“去,将史大人和十八位同考官都叫到这来。”
考官们汇于一所,那一份朱卷被轮流传阅,闻清远终于开了口:“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此卷算不算是违规,如何上奏,大家伙商量商量吧。”
他虽受了葛礼的托付,但这次的事情可谓开国以来第一例,自己决不能自作主张,更何况堂弟又不是儿子,倒也不必冒这么大的险。再者出了这样的事情,葛礼怨天怨地也怨不到自己头上。
那有儿子的史鉴倒是想把这份卷子打成违规,但事关重大在场没人敢妄下决断,他扫视众人,对闻清远笑道:“虽说这事儿定然是要上奏,最后由圣上决断。但我个人却觉得这是违规,若以数量取胜岂非开不端之风?倒不如我们联名上奏,附上大家伙的意见如何?”
闻清远闻弦歌而知雅意,附和一声:“本官赞成史大人的话,只是阅卷事大,不如先将其他卷子阅完,再联名上折子如何?这样对朝廷、对圣上都有交代。”
同考官们嗫嚅半晌,也不愿意搅和在这一场事儿里,还是随大流安全些,于是纷纷点头,等着阅完卷后联名具折,讲明事情后严斥此为投机取巧。
……
“……务多求进,全失制艺本旨。开钻营取巧之风,坏士林淳厚之体。文贵精纯,岂以多为胜?今若纵此浇竞,恐天下人群效诡术,弃根本而逐枝叶,圣贤之道渐湮,科举之公尽丧。”
乾清宫内,鎏金狻猊炉口吐出四合香浓浓的雾,一缕缕漫过蟠龙柱,沉、檀、乳、麝的芬芳中夹杂着一丝清苦,是掩盖不住的萦来绕去的药气。
皇帝年纪渐大,近些日子天热多用了些冰就患了伤寒,看那些弯弯绕绕的字竟然头昏眼花,只能叫太监吴祥念折子听。
最后一个字音消逝,崇德皇帝猛咳了两声,浑浊的眸子扫过跪在下边的端王、闻清远和史鉴几人,最后凝在纪禅的黑色常服上,苍老疲倦的声音模模糊糊地流出来。
“你也当了这次顺天府乡试的差,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端王手里还捧着朱卷,从后往前读了几篇时文,笑道:“儿臣倒觉得是两位大人小题大做了。此生虽有违程式,然心志可嘉,才学尤显,五经皆通极为难得,若此都要说成‘浇竞之风’,那岂不是说勤学刻苦为‘浇竞’?太过匪夷所思。”
“再者能一日之内书两万余字,岂是庸才可为?科举抡才大典,撰文多不应当是黜落士子的理由。更难得这是官卷,官宦子弟能这般励志向上,也够罕见的。”
“哦?官卷?”崇德帝倒有了几分兴致,史鉴眼睛狠狠闭上,心里暗骂:“就知道有这一出,现下如何是好?”
皇帝欣慰问道:“那倒真是了不得!他是谁的儿子?”
闻清远道:“是前吏部郎中段成平的儿子段之缙。”
端王惊讶,原来是这个小子,真真是有造化了。
可皇帝哪还能记着段成平这号人?端王补充道:“这是崇德十七年在赴任路上死难的山东玉平知府,原先是吏部员外郎。”
他这么一提醒,皇帝便记起来了,可惜道:“这一个两个的,都是水土不服,去山东那个死了,杨度也是上吐下泻又被调回了山东,身子太弱……那这么说,他父亲还对朝廷有功了?”
“正是。”
崇德帝大喜:“那应该大大的褒奖啊!亚椿刚看了那些文章,四书五经可通?”
亚椿是端王的乳名,《逍遥游》里说,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最是长寿,亚椿虽说为“不及椿树”,取得却是反义,算是文雅点的“狗剩”。
端王答道:“昌明博大有流转之致,虽不见如何精深,但破题极正派,的确是好好读过书的。不过这也是儿臣一人之见,到底如何还要请父皇裁决。”
语罢将朱卷递给吴祥,吴祥将朱卷呈上,皇帝摆摆手示意吴祥为他读。
听完一章,皇帝问道:“闻清远和史鉴觉得如何?”
闻清远是老油条了,听皇帝声音无一丝不耐又和顺慈爱便知是满意,正准备放弃给葛观澜说好话的时候,史鉴却憋不住了。
他到底是个翰林院没行过政的“尊贵人”,连圣上的脸色也不会看,梗着脖子说:“臣以为这些文字都难称得上是精妙。”
皇帝一愣,笑着看了一眼端王,而赞了这些文章昌明博大的端王眼里含着讥诮,倒要看看史鉴能说出什么高深之见。
“臣以为时文首要看是否集才情藻绘于一身,段之缙之文辞藻过于简明,到看不出什么精妙了。”
皇帝倚着吴祥的手喝了一口参汤,示意闻清远说话。
闻清远现在是死道友不死贫道,彻底抛了葛家的事情,正色道:“方才是臣等狭隘了,只忧虑会开钻营取巧之风,而没有考虑到五经皆通的难度。其文入理虽不如其他士子的精深,也可称为‘浩然一气’,极为流畅。更为难得的是一日之内书二十三篇时文,两万余字,便是点解元也是可的。”
史鉴
眼神一偏,用看叛徒一般的眼神看着闻清远,刚抬了下头便撞上端王深不可测的眼睛,倏忽间反应了过来,一时半会儿竟不知如何补救,胆战心惊地垂下脑袋。
皇帝视力虽模糊了,心思还灵明着,越是年纪大了越是老狐狸一样,下边的机锋一清二楚。
只是朝廷和家族是一样的,所谓“不痴不聋不做家翁”便是如此,轻不可闻地嗤笑一声,权当不知道。
刚才的参汤叫他提起了些劲儿,颇有些神采奕奕地问道:“既然段之缙可以点解元,其余的还有谁?”
闻清远是主考官,原本拟定的前十名聊熟于心,当即回道:“原本想要给葛观澜点解元……”
“葛观澜是葛礼的儿子?”
“正是。”
“哦……”皇帝沉吟一番,“官卷点了一个解元,其余的官卷就不要再进前十名了。除段之缙之外的前五名要习不同的经书,葛观澜调到第十一名去,官卷一共取五名即可,名次不要太高,但是国子监中的民卷若还有不错的,倒是可以往前调一调。”
轻飘飘地几句话就定了人家十年寒窗的成果。
闻清远称是,皇帝又看了看端王,“今年点了你做乡试的搜检王大臣,后日的鹿鸣宴你也去吧,跟士子们说说话……”正嘱咐着呢,吴祥禀报道:“皇上,方中堂求见。”皇帝招他进来,原来是工部修永定河大堤的事情。
科举的事情就先放到一边去,皇帝和方克城商量了一番最终定下,又突然想起来方家的嫡长孙也在国子监中,于是问:“你孙子今年乡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