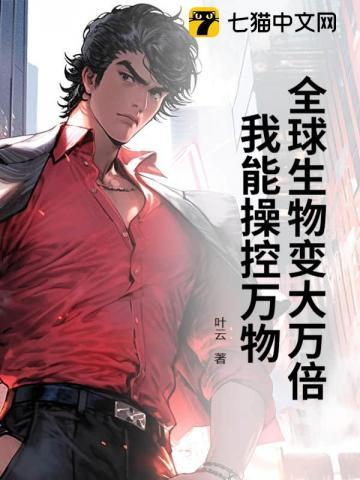吞噬小说>炮灰如何配享太庙(科举)阅读 > 6070(第8页)
6070(第8页)
续之以捐纳三益:权益救国、异途抡才和疏导士心,然后笔锋一转,才开始讲捐纳使得朝廷名器暗投、清浊莫辨和铨法紊乱的害处,最后提出三条更化之策。
一为严限捐途,禁止捐知县以上的实职,虚衔止于五品。二为设“捐员试政法”,捐纳者需历刑名、钱谷、河工三科历练,方得实授。三则正异相济,行“科捐并叙”,科甲出身者捐银可优先升转,捐员政优者准考御史。
写到这里,段之缙又从头看一遍对策,似无可补充之处这才开始结尾,写道:“用捐员如器使,控捐例如驭马,则国库可充而不伤根本,异途得进而不坏纲常。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再看第二问“各方边疆何以剿贼安民”,也是方才看得不甚仔细,段之缙仔细看了这才发现此题不光问对付西北赤砂人的对策,还将雍朝四方不臣服的异族都问了个遍。
国家广大,内部倒是安稳,边境却多有战火,小打小闹和如去岁一般攻城杀掠的战事都有。
西北赤砂野心勃勃,恐怕是想要入主中原,是朝廷的心腹大患。
西南高地的穹迦族是墙头草,雍朝势盛之时和雍朝交好,赤砂力强便与赤砂勾勾搭搭。
还有南诏百族聚集之地,一部分土司心悦诚服,另一部分明面上臣服,但是逆反之心不死,和汉人之间的矛盾也不小,前几年甚至有土司杀死朝廷官员。
而这些才是殿试想要问的东西。
段之缙顿感棘手。
三类边患中,他最清楚赤砂族,此前也都思考过这个问题。于南诏百族聚集之地的了解却没那么深了,能想到的只有改土归流等法。对穹迦族所知更少,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他们崇信神祇迦楼。
方才第一篇策写得长,千余字,许多贡士第二篇策问都已经写了一半,快者都去了左庑阶下交卷,而段之缙仍在纠结第二问。此时太阳挂在天正中,晒得他后背冒汗。
端王同王叔和几个兄弟坐在上方,自瞄到段之缙后眼睛一直盯着他,看他思考了这么久还未动笔心下纳罕。
这题他也是才知道,两问都不好写,可不好写随便写写便是,拖到后边天黑了可不好。
而此时,段之缙终于决定从明清的抚边政策中寻求出路,管他能不能用的,先写上再说。
于是他以“剿抚并济,分疆定制”为纲,先将三种边患分析清楚,再因时、因地、因人而分施刚柔之术。
对赤砂异族,要施展刚猛剿灭之策。剿灭之法却不尽是武力摧折,而要分而化之。目前赤砂大汗的王子有三人,其长子应当继承汗位,另外两个儿子征战沙场立再大功劳也无出头之日,不如暗中扶持,使其内斗。同时要在经济上严格限制,“凡汉商往北地贸易,一切铁器、粮食或丝葛棉麻均不得出境,违者
以资敌罪流放琼州。”
还要允许赤砂愿意归顺雍朝的平民百姓进我关内,与汉族同居同食,分与他们土地,叫他们不再过朝不保夕的日子,使其民心不齐不能成事。待到时机成熟就立刻发兵剿灭。
对于穹迦族则要施展怀柔分化之策,一是遣使问顺,若其大喊愿意归顺,则赐以王印,“许其世袭罔替,然须送质子入京习礼。并置有司于神山,设流官掌茶马五市、驿站通衢,穹迦头人理刑狱祭祀,各司其职。”倘若不归顺,仍要尽量安抚,赐予金钱宝物,宣示我天朝上国之仁爱。
二要大肆宣扬佛教,若有改信者朝廷赐予土地金银,若有头人或大汗之亲属情愿改信者,可封其为“大法师”,诱诸部改宗相攻。“俟其内部相攻,而我朝坐收渔翁之利……”
写到此时,太阳已经转到了身后,周围同年业已走净,唯一的光亮也就剩下那点残阳,段之缙袖子拂去额上的汗,睁大眼睛奋笔疾书。
殿内,誉王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吩咐殿内的太监孙鹤林:“你去催催他。”
孙鹤林方要去,又被端王唤住,“殿试本来就是一日的时限,催人家只会叫士子心焦。”他笑着看誉王,“二哥,急什么啊?您要是耐不住就先回去呗,父皇那儿弟弟去说。”
肃王和誉王闹做一团,四哥又常帮他,自然站在纪禅这边,朝着誉王挤眼睛,当着大家伙的面讥诮道:“可是王府里娇妻美妾等不及?”
誉王瞪了他一眼不爱跟他吵嘴,端王看看外边的日头吩咐孙鹤林给段之缙掌灯。
“去给他挑得亮一些,别看坏了眼睛。”
段之缙视物已经不甚清楚,索性最后的南诏已经在心中打好草稿,定然能在太阳落山之前全部书完,而就在此时,一盏灯在旁边亮起,最后放置在自己案上。
孙鹤林笑着道:“这是端王爷叫来送的灯,吩咐你慢慢写,慢工出细活呢。”
段之缙感念非常,谢过王爷和孙鹤林后接着写最后一段。
针对南诏百族聚居之地,要行刚柔并济之策。南诏百族本身就非为铁桶,对于真心归顺朝廷的要大大褒奖,对于反复无常甚至杀害朝廷官员的土司则要杀鸡儆猴。但最终都要改土归流,不能叫土司之职继续存在。同时还要从文教方面入手,“编《百族正音》,将土语音调标注汉字,命蒙童先习官话再学土语,使南诏之地无复土语相闻,但有弦诵之声。”
最后落笔,“臣管窥之见,伏乞圣裁。”
终于,殿试结束了。
段之缙先向殿内一拜,带着卷纸走到左庑阶下,受卷、弥封等官俱在檐下等候。
打个哈欠,受卷官将那一摞纸接过,登记后交弥封官,段之缙则由鸿胪寺官员领出皇宫,此后只等着金榜题名日的到来。
第66章066双喜临门
殿试之后便是阅卷,四位中堂大人和各衙门的阅卷官都住在文华殿左右两廊和传心殿前后房间内,三日阅卷结束后才许回家。且每位阅卷官每一篇策问都要看。这十几人中以毓秀中堂为首。
阅卷还未至一半,方克城松快松快肩膀,“今年的题着实不好写,诸生的对策大同小异,二三百字的策也忒多了些,颂圣的策也多。”
毓秀哆嗦着手把鼻梁上的眼镜往上抬抬,“是吗?我倒是看了几篇不错的,对赤砂人了解很深呢,对付南诏的改土归流之法我看很不错。”
旁边的刘玳廷抬起佝偻的身子,“哦,老中堂也看到那篇了?的确是条对详明,篇幅充畅,我看今年能点做魁首。”
“当真有这样的学生?若是你们阅到了,可得叫我看看。”方克城话音方落,大理寺正卿颜正便招呼他过来,“大方中堂,在我这儿呢。”
两个人凑头共阅,都觉得这篇可定为魁首,便接着上边的“圈”勾圈。
三日后阅卷完毕,那改土归流之策是少有的全圈之文,几个大人商量着以其做魁首卷,在黄签上书“拟第一”。
素来的成法,呈进殿试卷于传胪前一日,因为是“天子门生”,因而这前十名要由皇帝钦定,又因为皇帝要召见这前十名,因而这一日又称为“小传胪”。
小传胪当日,段之缙等贡士于午门外等候。
今天天气极好,天色湛蓝,万里无云,太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睛。
朱红色的大门嵌着拳头大的今钉,赤红色宫墙高高耸立,段之缙的心跳不由得乱了一拍。
等了没有多长时间,毓秀大人从午门走出,招呼这十名贡士上前,“陛下的恩典,今日太阳刺人,你们随我进乾清宫等候吧。”
长长的宫道上,每隔几步都有侍卫持刀守卫,洒扫太监见他们走来,远远避开。
毓秀跟乾清宫门口的太监说了几句,太监就进去通传,不一会儿吴祥打开宫门,先笑着跟毓中堂打招呼,才领着众人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