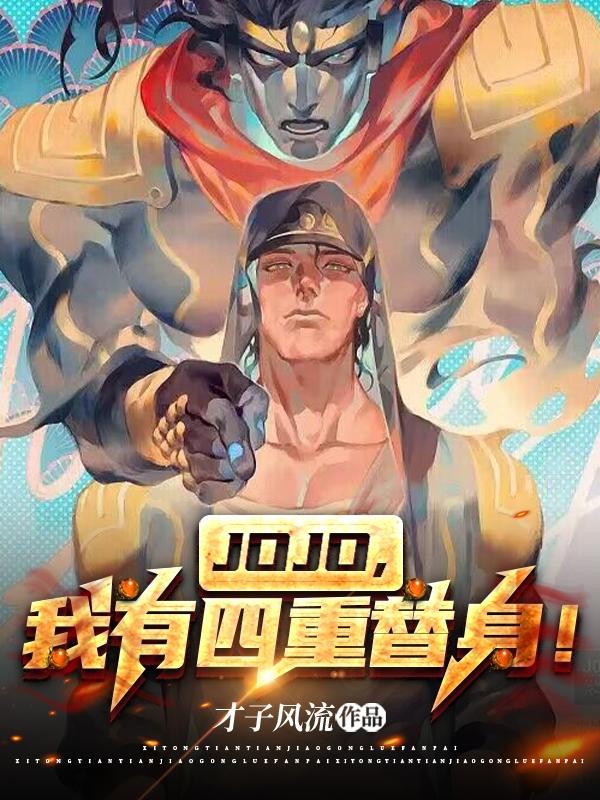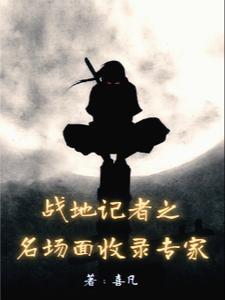吞噬小说>将地府改造成游戏 > 90100(第11页)
90100(第11页)
是啊,他在顾虑什么?他总不能告诉郭淮,从近几回往来的书信看,洛阳的小皇帝恐怕已经对自己产生了不可解释的阴暗猜疑,君臣之间的关系渐趋紧张,很多事已经不好开口?他也总不能明示上下,如果他上书求援,暴露软肋,那就算真的得到了皇权的援手,地位与权势也必然会一落千丈,再难复起?
葬送他一人的利益,稳定的却是小皇帝的地位,这样的买卖,凭什么要做?
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小皇帝已经明白无误地展现出了猜疑,那司马氏当然也没有什么单方面付出的舔狗心理。大家面热心冷,彼此算计,一饮一啄,无非因果,又何必指望什么尽忠职守?想让司马侍中冒险效忠皇权,那纯粹想多了。
自然,如此阴冷的算计是不能示人的,所以司马氏稍稍沉吟,立刻露出了微笑:
“我也是为了大局着想。”
郭淮不解:“大局?”
“是的。”司马懿早有成算,所以不慌不忙:“以现今的局势,如果强行下旨,必然重违军心;就算圣上能强力弹压下来,无疑也会招致士卒的怨恨。这样替君上树敌的事情,当然要谨慎又谨慎。”
他停了一停,又道:
“尔有嘉谋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谋斯猷,惟我后之德。’!”
这是《尚书》中的名句,讲的是为人臣子要忠心君上,有了什么好谋划好计策,应该归功君主;有了什么过错疏漏,要设法自己弥补;这才是效忠君上应有的方略。司马懿引用如此名句,无疑是暗示了自己的态度——如果明知道下旨弹压会损害皇帝的威望,那他们这些做大臣的又怎么能视之不见,诿过于上呢?
这一句分辨很合理、很有力度,仿佛真是一片拳拳之心,在真真切切的为皇帝着想。如此情真意切,以至于郭淮都愣了一愣:
“将军是说……”
“皇帝还小嘛。”司马懿叹息道:“当然要替他多考虑考虑。”
这样的和煦,这样的忠厚;这样的端方,这样的正直;尤其是司马侍中说完理由,随即微微侧首,让烛光照亮了他垂落的几缕白发,以及额头隐约的皱纹——那是司马侍中早上起床后精心修饰,特意挑出来的白发——于是,那种慈蔼、忠贞,烛光中の托孤重臣的形象,呕心沥血的忠臣楷模,便跃然眼前,再也不可忘怀了。
郭淮感动了:
“可是将军,如此一来,军中的压力,不就……”
不就全落在司马侍中一个人头上了吗?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我受先帝托孤之重,总要多担待担待。”司马懿很温和、很镇定的说:“再说了,只要有利于国家,有利于至尊,我个人的荣辱,不过如天地间一片落叶,又何足道哉呢?”
“将军!”话到了这一步,郭淮实在不能不动容了。他猛地站了起来,语气已经极为激动:“将军之心,何等光明;将军之行,何等磊落!有将军这样的贤臣,是大魏社稷之幸呐!”
面对这样的赞美,司马侍中淡淡一笑,尽显雍容:
“伯济太过誉了,老夫惶恐不胜。“
第99章
郭将军的敬佩是真诚的,他真心实意的认为,司马侍中为了维护少帝的权威,是不惜填上自己的威望与声名,也要竭力与蜀军周旋到底。这样的拳拳忠贞、一片热忱,真是令他感佩而且羞惭,大大的自愧弗如,憧憬之意,更是油然而生。
都说西川的诸葛氏忠贞不渝,是人臣的表率;我们大魏的托孤重臣也不差了什么嘛!先帝托付得人,想必在九泉之下,也当大大感动吧?
不过,心绪的起伏无助于解决实际的困境。郭将军发自真心地敬佩了片刻,还是小心开口:
“可是将军,如今蜀军毕竟势大……”
是的,司马侍中愿意为了少帝不计荣辱、慨然承担,确实是千古难有的佳话。但佳话归佳话,再这么僵持下去,侍中……侍中他老人家撑得住么?
士气濒临崩溃,局势更是不利;无论从哪个方面推敲,都实在看不到希望的曙光。须知,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真要在前线丢盔弃甲一败涂地,那压力不还得给到后方的皇帝?
显然,司马侍中对此亦早有成算,他不慌不忙,微笑着称呼郭淮的字:
“伯济不必过虑!”他道:“其上如风,其下如草;如今军中人心惶惶,无非也是草随风动,被一时的困局所震慑而已。小人之心,何足挂齿?只要能打几场小小的胜仗,他们自然会回心转意,体会到上面的苦心。”
郭淮:“……胜仗?”
郭淮的面色变得古怪了——他当然知道胜仗能解决一切思想问题,军中有点脑子的都知道胜仗能解决思想问题;可是吧,要是他们能随随便便打个胜仗,那还至于现在坐守孤城,愁眉不展么?
这样的高谈阔论,言之凿凿,和废话有什么区别?
即使面对如此奇特的神色,司马侍中城府极深,依旧安之若素。他道:
“要想一击克敌,犁庭扫穴,那自然是千难万难;但以老夫的见解,抓一抓蜀军的弱点,打几个不大不小、足以挽回士气的胜仗,应当还是有可能的。”
郭淮诧异:“蜀军的弱点?”
——他怎么没看出来蜀军有什么弱点呢?或者说,要是蜀军真有什么了不得的弱点,您老何不早点下手,一击毙命,还至于苦巴巴等到现在?
“蜀军军势严整,的确无缝可寻。”即使司马懿脸皮再厚,亦不能不承认老对手治军的精密手腕:“但两军对垒,非唯人力,亦关乎天数。蜀军行兵列阵,整整有法,但天命不佑,又何惧之有?”
他停了一停,低声道:
“伯济应该知道,诸葛氏的身体,可一直算不上怎么好。”
郭淮终于悚然变色了:
“……将军是说?!”
“西川的使者来的时候,我问过他诸葛氏的起居。”司马懿缓缓道:“他虽然遮遮掩掩,但话风中依然可以听得明白,诸葛氏一天的饮食,也不过是三升米、一点脍肉、一点菜蔬而已;此人谨慎自持,二十罚以上,都要自己省览;如此食少事繁,岂能久乎!蜀军的军势,或者没有太大的破绽;但诸葛氏的身体,就是他们最大的破绽!”
没错,先前西川使者大摇大摆,上门激将之时,司马懿严阵以待,也不是没有预备。他抢先过问诸葛氏的饮食,正是在话语中打了个极为阴险的埋伏。如果使者说诸葛氏一天食米三四升,他就说此人“食少事繁,岂能久乎”;如果使者咬咬牙,谎称诸葛氏胃口极好,一天两斤炖肉三个肘子四斤黄酒,他就说诸葛氏胡吃海喝毫无节制,迟早飞升三高星球;如果使者聪明一点说诸葛氏营养均衡饮食精细,吃的是蒸羊羔蒸鹿尾蒸熊掌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等等美食,他就说诸葛亮饮食奢靡、略无顾忌,俨然亡国之相,依旧还是药丸。
总而言之,无论使者回答什么,司马懿都有万全的准备,一定能把话题转到“岂能久乎”的固定结论上;靠着洗刷西川使者来洗刷诸葛氏的威慑力,为军队挽回一点虚无的信心——既然敌军的魁首已经“岂能久乎”,那己方自然是“坚持下去,就有办法”嘛。
但很可惜,他接见时刚刚开口问了两句,那个西川的使者就忽然发作,抽出了女装当场敬献,搞得司马侍中立刻破防,不能不厉声把人驱逐出去;连预备好的妙妙小话术也被直接斩断,根本来不及施展;以至于只有在如今故技重施,为郭淮论证诸葛亮的“岂能久乎”。
显然,郭将军还是太忠厚了,根本没有意料到主将会隐伏下这样无懈可击的妙妙论证。他甚至还认真想了一想,然后发现司马侍中的理论居然还相当合理——毕竟,诸葛氏天天坐个三轮车到处逛的事情大家也是知道的,要是身体健壮行动自如,何必天天坐三轮车?以此观之,在经历了军旅冗杂事务的折磨之后,说一句“身体虚弱”,也是相当正常的吧?
“我前几日得到线报。天水陷落投降以后,诸葛亮亲自赶赴前线,安抚军心。”司马懿缓缓道:“自汉中至天水,沿途奔波数百里之遥,又都是崎岖的山路,以诸葛亮的体格,又能支撑多久?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机会,不能不牢牢把握。”
以当下的生产力,“旅途劳顿”可绝不是什么夸张;就算是皇帝巡游,筹备完全,一天走上百余里也要疲惫不堪;何况军中诸事皆简,遭受的磨折更比寻常厉害百倍。诸葛氏长途奔驰之后难以克当,为此生一场大病都是有的。而以蜀军现在的情形,唯一一个可以支撑大局的顶梁柱病倒,肯定也会露出极大的破绽。所以司马侍中口中的“缝隙”,真不是什么虚妄之言。
郭淮面色微变,再明显不过的露出了心动。被蜀军摁在前线憋屈了几个月,魏军上层的郁闷与不快同样抵达了顶点。平日里为了顾全大局,尚且可以暗自隐忍;如今真有了一举翻盘,争夺胜利的良机,又怎么能轻易放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