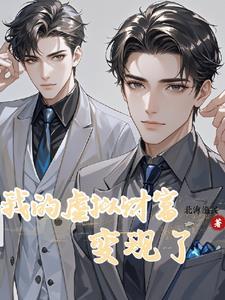吞噬小说>卿卿如许是什么意思 > 第6章(第1页)
第6章(第1页)
>
“许…许小姐,”她的中文发音有些僵硬,“请相信,现代修复技术非常了不起。苏黎世大学医院……”
我抬起另一只缠着纱布的手,轻轻推开了那面即将映照出我此刻模样的镜子。
动作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拒绝。
纱布底下,新生的皮肉绷得很紧,纵横交错的痂痕盘踞在颧骨、下颌,一直延伸到耳际,像数条狰狞僵死的暗红蜈蚣,带来粗糙的摩擦感和深及骨髓的痒痛。
“不必了。”我的声音透过纱布传出来,有些闷,却异常平静,
“留着吧。这是…新生的印记。”
护士张了张嘴,最终只是沉默地点点头,收起了镜子,动作更轻地替我更换新的敷料。
消毒水的气味弥漫开来。
挪过来的资金在离岸账户里安静地流淌了半年。
当阿尔卑斯山脚那个宁静的小镇迎来第一场盛大花季时。
一个名为“萤火”慈善基金会低调地注册成立。
名字是周叔起的,他说,微光汇聚,也能照亮一点方寸之地。
很符合我此刻的心境——不耀眼,但存在。
基金会的事务繁杂而具体,审核项目,拨付善款,追踪落实。
日子像山涧溪流,在规律的忙碌中潺潺向前,冲刷着记忆里那些粘稠的血色和锥心的痛楚。
脸上的疤痕渐渐软化,颜色变浅,成了一种顽固的、凹凸不平的浅褐色地形图,被昂贵的遮瑕膏和高领衣衫小心地掩藏。
瑞士的医生说得对,现代技术确实了不起,至少能让这张脸在远处看起来,勉强算得上“正常”。
直到那份来自巴沃那山谷小镇的项目申请,带着当地泥土和风雨的气息,沉重地落在我的办公桌上。
照片拍得极其简陋:几间墙体开裂、仿佛下一秒就要被山风揉碎的土坯房,屋顶的茅草稀稀拉拉。
唯一能称之为“窗”的洞口,糊着破碎的塑料布。
然而,照片中央,一群孩子挤在昏暗的“教室”里,眼睛却亮得惊人,像坠入凡尘的星子,穿透了破败的环境,直直地看向镜头之外。
负责此地的联系人,是一位华人支教老师,名叫历飞羽。
申请报告是他一笔一划写的,字迹清隽有力。
详细描述了学校面临的困境:屋顶漏雨,墙体倾斜,没有像样的课桌椅,更没有一本课外书。
资金的缺口触目惊心。
报告末尾,他附上了一段话,没有诉苦,只有平静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