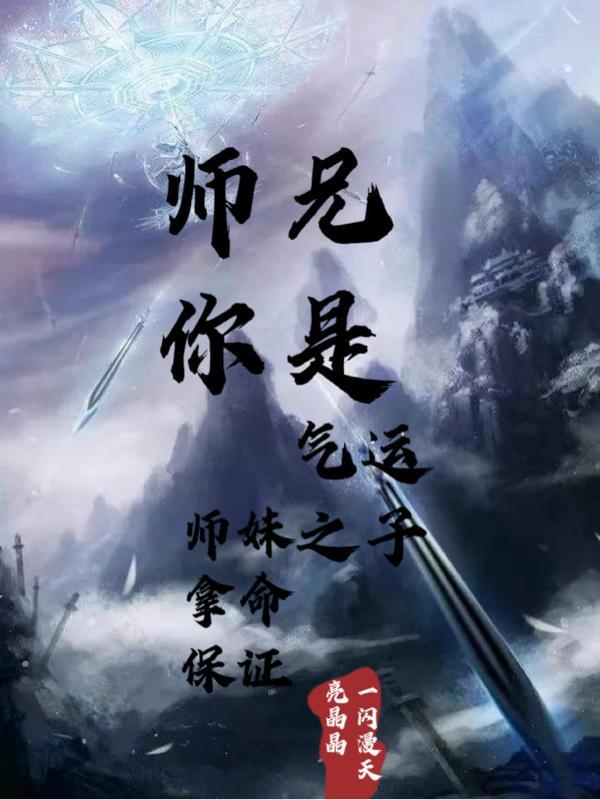吞噬小说>王爷盛宠带着系统做神医 > 第104章(第1页)
第104章(第1页)
&esp;&esp;裘智不疾不徐地答道:“麦角毒素的潜伏期较长,少则数天,多则几周才会发作。守宫被囚禁在灯笼张家三日,每天以米度日,八成就是那时中的毒。”
&esp;&esp;他顿了顿,继续道:“哑仆是灯笼张的厨娘,最方便下毒。但她的目标并非守宫,守宫只是殃及池鱼。”
&esp;&esp;朱永贤听得目瞪口呆,脑子一时转不过来。他怔了一会儿,才咋舌道:“可哑仆为什么要杀灯笼张?他们不是一伙的吗?”
&esp;&esp;裘智沉吟片刻,猜测道:“我怀疑哑仆就是那个采药人。至于具体原因,我不太清楚了。不过这种骗子团伙,内斗也是常有的事。”
&esp;&esp;这个答案完全出乎朱永贤的意料。他震惊不已,心中涌出无数疑问,一时不知从何问起。过了半晌,他才勉强理清思绪,追问道:“你是怎么猜到的?”
&esp;&esp;裘智微微一笑,解释道:“其实,最初大姐说她们被灯笼张关在屋里时,我就觉得奇怪了。灯笼张这么多年都行为鬼祟,哑仆为什么直到最近才怀疑他不是好人?”
&esp;&esp;朱永贤点了下头,只听裘智缓缓道:“而且,灯笼张这次的骗局手法太过粗糙,与他过去的精妙布局有天壤之别。我怀疑,凶手知道他命不久矣,所以懒得替他谋划了。”
&esp;&esp;朱永贤猛地睁大眼睛,失声道:“难道之前的骗局,都是哑仆想出来的?”
&esp;&esp;裘智迟疑道:“这只是我的猜测,哑仆表现得太过单纯,骗局又和之前的完全不同。反正她们都在牢里,迟早能水落石出。”
&esp;&esp;朱永贤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随即又皱眉道:“可哑仆不是女的吗?她怎么可能是采药人?”
&esp;&esp;裘智解释道:“哑仆上了年纪,冬天衣服又厚,她一身男装,以斗笠遮脸,根本看不出性别。采药人声音沙哑,非常有特点,只有装成哑巴,才能避免别人将她与采药人联系起来。”
&esp;&esp;朱永贤听到这里,气得一拍大腿,愤愤道:“这哑仆真是心机深沉!一直以哑巴形象示人,就算东窗事发,也没人会想到她就是采药人!”
&esp;&esp;说完,他转头看向裘智,眼中满是崇拜,虚心请教道:“你是怎么发现这点的?”
&esp;&esp;裘智唇角微扬:“她今日进入大堂,听到你的身份后,立刻行四拜礼参见,不像寻常妇人。”
&esp;&esp;他第一次见朱永贤时,尚且不知如何行礼,何况一个民妇?哑仆举止有度、礼数周全,实在让人生疑。
&esp;&esp;裘智立刻留心上了,采药人眼力极佳,仅凭衣着、言行便能判断一个人的富贵,哑仆熟知礼仪,不免有所联想。
&esp;&esp;念及此处,他不由回忆起初见朱永贤的场景,心头微微一暖,嘴角不自觉地浮起一抹笑意,目光柔和地望向他。
&esp;&esp;朱永贤并未察觉裘智的情绪变化,但看到他眼底的温柔,心中一阵甜蜜。他轻轻握住裘智的手,微微一笑,顺势将头靠在爱人的肩上。
&esp;&esp;裘智微微一怔,片刻后轻笑一声,手臂微收,将朱永贤抱得更紧了些,才低声道:“还有一点。灯笼张每次藏银子出门前,总要将几人分开锁起来,为什么不干脆把他们关在一起?”
&esp;&esp;朱永贤抬眼看他,似乎在等待答案。
&esp;&esp;裘智继续道:“我怀疑他和哑仆关系不同寻常,每次都会带着哑仆一起去藏银子。他担心大姐和八妹猜到哑仆与他是一伙的,故意将姐妹二人分开囚禁,制造出‘三人都被分开关押’的假象。可实际上,被关起来的,只有姐妹二人。”
&esp;&esp;朱永贤听得连连点头,恍然道:“原来如此!看来那包珠宝也是哑仆精挑细选的。”
&esp;&esp;哑仆和灯笼张本来就是一伙人,又眼力不俗,轻而易举就能挑出最值钱的珠宝。
&esp;&esp;他顿了顿,又忍不住问道:“哑仆和灯笼张到底是什么关系?”
&esp;&esp;裘智耸肩道:“这得让李尧彪他们去查。如果灯笼张年轻时就开始行骗,那他和哑仆合作的时间,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久。”
&esp;&esp;朱永贤思索片刻,忽然轻叹一声,感慨道:“她还算有些良心,认下了杀人一事,没有让大姐和八妹送死。”
&esp;&esp;裘智闻言,忍不住失笑,伸手揉了揉朱永贤的头发:“你太天真了。”
&esp;&esp;朱永贤立刻拍开他的手,撒娇地哼了一声。
&esp;&esp;裘智笑道:“李尧彪办案粗枝大叶,连物证都能弄混,最初估计也没想着把三人分开,给了她们时间串供。”
&esp;&esp;他在背后说李尧彪的坏话,多少有些不自在。对方是皇城司的镇抚,万一有耳目听到了,汇报给李尧彪,下次见面难免尴尬。
&esp;&esp;裘智停顿片刻,才继续道:“三人没办法串供得太详细,因此证言漏洞百出,稍有经验的官员就能察觉破绽。而且,若不解剖尸体,根本无法发现灯笼张曾经中毒。”
&esp;&esp;其实裘智觉得,就凭卫朝仵作的水平,哪怕解剖了,也看不出灯笼张中毒。